
春节假期,年轻人“断亲”的话题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年初四(2月13日),关于“农村悄然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断亲”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话题阅读量破亿。有学者将年轻人“断亲”总结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即所谓的“不走亲戚”。
“断亲”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关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宗昊在去年刊发的论文《“断亲”:概念、问题及思考》中指出,伴随着城市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生活压力与内卷以及数字化生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断亲”。上述研究得出结论,“断亲”是现代化的结果。
如若“断亲”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征,那么其他同样经历了剧烈社会转型的国家出现类似情况,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韩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21世纪初就注意到了韩国家庭纽带日渐松弛的情况,它具体表现为避免、推迟、减少、逃避家庭责任和家庭关系,如生育率急剧下降。“种种迹象表明,韩国人正在极力回避家庭关系和由此带来的负担,”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一书中写道。
中韩同为有着深厚儒家文化传统、重视家庭的实际和象征意义的国家,因此,理解韩国社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作为“压缩性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理论的提出者,张庆燮认为,同为追赶西方现代性、为所处劣势感到不安焦虑的后发国家,“压缩现代性”是亚洲国家共同的地区特征。“压缩现代性”具体表现为“国家政体、官僚机构、工业组织、地方社区、学校和家庭,都受到‘传统+现代+后现代’和‘本土+西方+世界主义’等奇怪的混合意识形态的支配”。
很大程度上来说,家庭已经成为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冲撞最为激烈的场域。张庆燮在书中指出,韩国一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结构改革,另一方面又坚持强烈的家庭中心主义。韩国压缩现代性的许多局限和问题,实际上与家庭密切相关,即家庭必须承担各种家庭意识形态所需的不同角色和功能,令家庭成员不堪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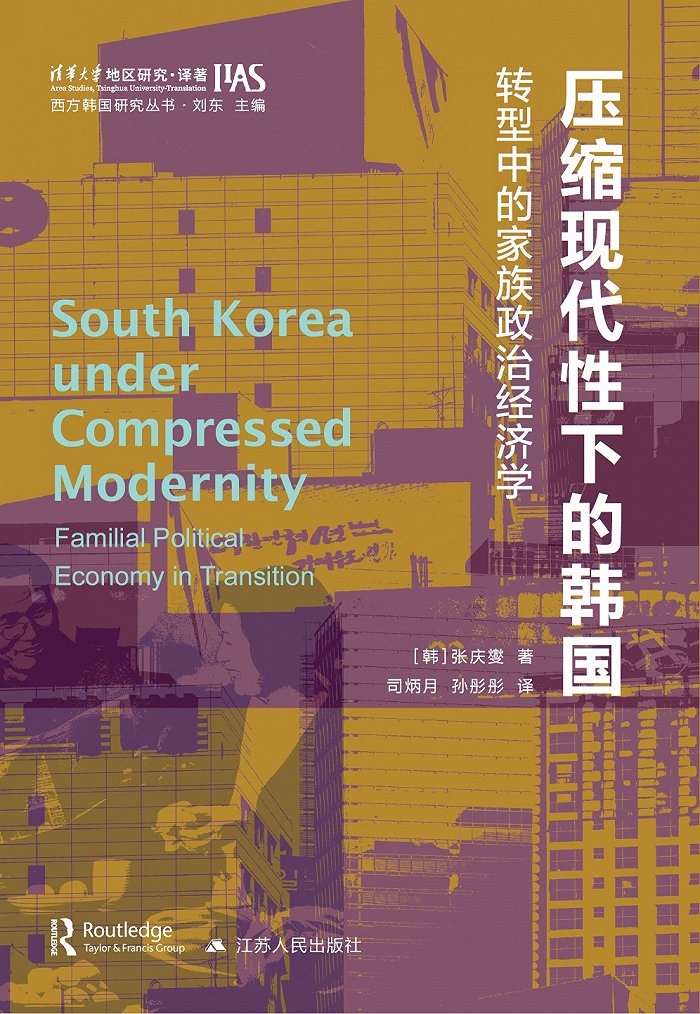
韩国的“家庭危机”发生于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快速实现经济发展,韩国采用“先增长,后分配”的生产主义战略,对社会再生产(即保护、培育、管教、安抚和帮助人类的社会活动)的立场可以概括为“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将这一部分责任最大化地转移给家庭。于是,韩国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实现的经济腾飞建立在家庭的巨大付出上——韩国家庭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竞争中全力支持家庭成员,成为促成其成员在社会上成功的主要工具。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家庭亦为国家准备了大量工业化所需人才,分担了大量照料老人、儿童、残障等弱势群体的责任。
经济飞速增长和产业急剧转型意味着不同行业、地区、职业、世代的生命经验迥然相异,传统(本土)价值观和制度与现代(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共存,却缺乏协调整合,导致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中表现出偶然多元性(acceidental pluralism)的文化失序状态。张庆燮认为,与公共领域几乎被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一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截然不同的是,家庭领域存在价值观多元和制度多元的显著情况,“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甚至后现代文化并存,不同世代接触到这些文化的程度不同,导致代际关系紧张,冲突不断。”
根据张庆燮的分析,韩国社会存在四种主要的家庭意识形态——儒家家庭主义、工具家庭主义、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儒家家庭主义的核心是对朝鲜时期传统家庭价值观和规范的继承,这种以道德等级为基础、维持两性和代际关系的家庭意识形态,依然对当代韩国人产生最主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儒家家庭主义将女性和年轻人置于家庭等级制的底部,这两个群体对这一家庭意识形态的反感也在增强。

工具家庭主义指的是韩国人将家庭视作实现社会成就的主要工具、积极调动家庭资源和亲属网络的观念与做法。这是韩国人在动荡的20世纪摸索出来的生存策略和人生哲学。
情感家庭主义最初产生于西方,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动荡中号召人们重建家庭,使其成为人们的情感避风港,以应对工业社会造成的人与人的疏离。在韩国,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使得情感家庭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在中产阶级中迅速流行开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情感家庭主义将夫妻关系的优先级置于其他关系之上,它对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主妇)的感召力尤其强。
社会民主化促进了女性和青年的个性发展,消费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带来了家庭生活商业化,个人主义家庭主义随之开始出现。它特别体现在,越来越多女性认为参与劳动市场比进入婚姻和家庭对自己更为有利,结婚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而非必须。
国家对家庭的依赖加剧家庭危机张庆燮发现,韩国家庭文化不是线性发展变化的,而是多种家庭意识形态共存,根据年龄、世代、性别、地区、教育程度、阶层等因素的不同而分布各异。整体而言,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城市居民和女性更加倾向于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而其他群体则更加倾向于儒家家庭主义和工具家庭主义。
“整个社会,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要同时维护各种不同的家庭意识形态,过着复杂而暴躁的生活……这是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韩国的、东亚的、西方的、全球的等多种宏观社会趋势偶然并存的直接体现。正是这种偶然多元性从根源上造成了韩国人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困境。”
张庆燮指出,国家对家庭作为社会运作根基的依赖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韩国的家庭危机。官方家庭政策一直以来试图保留家庭的(新)儒家性质,以便依靠家庭职能和职责来获得社会支持,特别是鼓励私人家庭在不要求国家援助的情况下,抚养、保护、教育、管教、抚慰、支持和照顾其成员。截至1990年代,韩国在社会保障上的花费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支出水平的1/10-1/5。由于强迫私人家庭承担繁重的社会再生产任务,韩国家庭出现了“功能过载”,不堪重负,韩国社会无止尽的教育“军备竞赛”即为一例。

面对家庭意识形态多元共存、彼此冲突的情况,国家和社会并未深入分析种种张力之下的真正问题,而是以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观点,对致使稳定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人进行道德批判。许多官僚、政客、学者和记者认为,核心家庭的崛起和增加滋养了个人主义式的自私自利,破坏了传统家庭的团结与稳定,从而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久而久之,这一观念被许多韩国人内化了。在张庆燮看来,
“韩国人不习惯把家庭负担和痛苦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他们对家庭事务的关注往往使他们无法判断抚养、保护、教育、支持和照顾公民是国家的责任,或者判断出这些是‘公民权利’。保守派官僚和政客也无法设计一个严肃的福利国家计划来减轻家庭的功能和情感负担。”
可这不能阻止韩国人为减少家庭生活的压力、疲劳和痛苦带来的损耗,避免、推迟、减少、逃避家庭责任和家庭关系,造成了所谓“去家庭化”的倾向。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并不是韩国去家庭化中唯一一个严重征兆,许多其他征兆——如离婚、分居、离家出走、晚婚和单身现象——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如张庆燮所说,“由于越来越不利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许多当代韩国人在各个方面都因家庭主义而受到谴责,他们必须孤注一掷地进行抵抗行动,这导致社会和人口出现去家庭化倾向。在这方面,个体化甚至可能成为解决韩国人口和经济微观社会可持续性危机恶化的潜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