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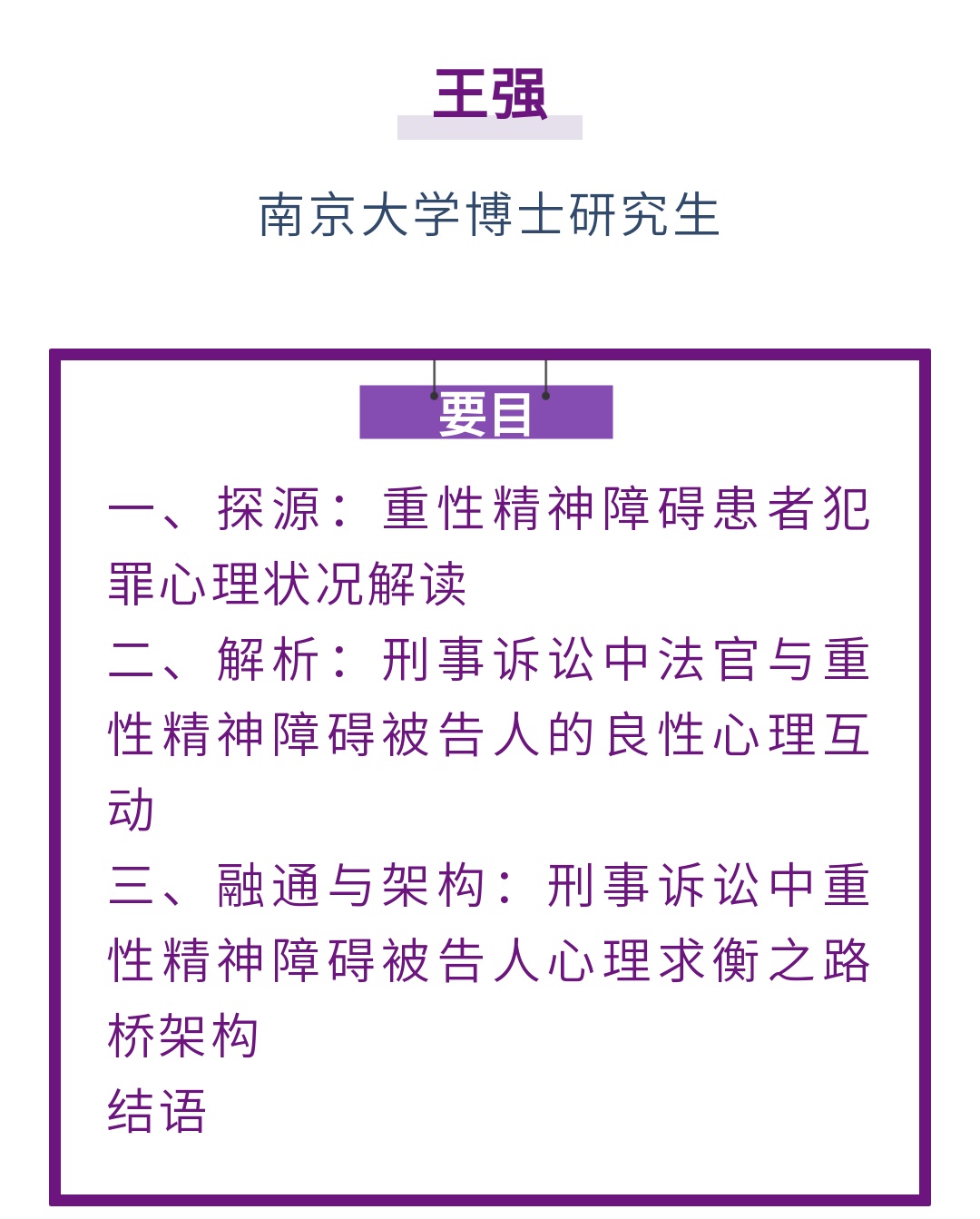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暴力危险性较高,南京白事一条龙4000253450刑事诉讼中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精神行为异常,扰乱庭审秩序,或伤害诉讼参与人,或妨碍司法公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了解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心理是解析其诉讼心理的前提要件,法官主导的诉讼心理良性互动是诉讼程序顺利推进的必由之路。为保证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参与的刑事诉讼案件诉讼程序能顺利推进,平衡诉讼当事人的矛盾心理,法官在诉讼中有必要引入心理学理论与技术,掌握常用诉讼心理融通之技;同时,完善类案程序机制,推进“专人专技”的诉讼辅导制度落地,最大化实现类案诉讼高效有质的“案结事了”。

2013-2015年,全国范围内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得出我国精神障碍12个月患病率为9.3%、终生患病率为16.6%,而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660万人。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特殊群体,其在社会中的体量逐渐增大,涉及精神障碍患者参与的刑事案件数量亦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随着我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体系的构建,心理学技术在司法实践的运用虽然得到重视,但也表现出了后劲不足之态势。首先,法官对精神障碍的认知率低。绝大多数法官限于知识壁垒,缺乏熟练识别精神障碍的能力,“导致仍有数量较多的严重心理障碍者(可能的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未被认识并作做进一步处理”。其次,心理学相关技术与诉讼程序嵌入不佳。结合司法实践的理论研究,心理学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如多道心理生理测试技术、心理痕迹分析技术、犯罪心理画像等技术,而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应用研究较少,以“诉讼心理学”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2013—2022年仅有22篇学术文章发表。最后,心理学相关专业人员储备不足。我国目前精神科医生仅有3.4万人,相当于每十万个人中只有两位精神科医生,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需求,要想在诉讼程序中引入心理相关专业人员,属实困难。
反观域外,心理学技术或相关专业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应用较为成熟且颇为频繁。在美国,一方面法律允许律师影响陪审团成员的遴选,“在陪审团成员的遴选过程中,心理学家会指导律师在可选范围内选择对己方有利的陪审团成员”。另一方面,美国精神卫生法庭的设立被视为近年来精神卫生法领域最重要的进展,精神卫生法庭最具特色之处在于程序参与人的角色改变,尤其是法官。法官突破“裁判者”的传统角色,转变为“治疗者”,而这也对法官自身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德国,早在1800年左右,随着司法酷刑的废除,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将心理学作为解决刑事司法实际问题的方法,如在19世纪早期,法律研究者认为对犯罪嫌疑人的道德谴责(the moral exhortation of the suspect)可以作为一种心理工具,“扰乱犯罪嫌疑人的心态”。
庭审过程是诉讼双方为达到自己的诉求预期相互博弈的过程,难免存在冲突,相较于一般场所,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的情绪更容易受矛盾的激化,阻滞庭审的推进,妨碍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如某法院代理审判员孙某某、书记员闫某某在对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进行宣判时,被告人王某(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遗留精神障碍)因对该判决不满,当庭对孙某某、闫某某进行谩骂,撕碎宣判笔录及送达回证,并随即用拳脚殴打孙某某、闫某某,致孙某某头皮血肿及口唇黏膜破溃,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仔细斟酌,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参与庭审可能会带来如下影响:一是“静”,一言不发,呆若木鸡,对法官、检察官甚至自己的辩护人的问话总是爱答不理,“安静”的让庭审难以继续;二是“躁”,胡搅蛮缠,出言不逊,情绪失控,扰乱庭审秩序,进而阻滞诉讼进程,延长诉讼期限;三是“拗”,固执己见,罔顾证据和法律,盲目提起再审、缠诉、重信重访,损害司法公信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涉及精神障碍患者刑事案件数量的增长,或是审判活动中诉讼心理技术和人员参与的重要性,还是为更好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精神障碍患者参与的庭审过程都对法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执业要求。为此,从犯罪心理学、诉讼心理学理论出发,结合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参与庭审的司法实践,挖掘法官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心理互动历程,为法官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心理技术指引,确有研究之必要。
一、探源: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心理状况解读
近年来,随着精神障碍患者人数的增加,精神障碍患者犯罪也有增长之趋势,了解重型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心理,是从源头攫取诉讼心理形成机制。诉讼心理的形成不仅存在于诉讼过程之中,犯罪嫌疑人犯罪时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原因亦是法官识别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诉讼心理的重要支撑。在此,笔者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特征、犯罪心理原因出发,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心理状态进行解读,以期从中寻求诉讼心理求衡之良方。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通常具有犯罪动机离奇多样、犯罪方式残忍、犯罪结果危害性大以及犯罪的随意性和偶然性等特征。犯罪动机的离奇多样可能是因为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犯罪嫌疑人失去了对现实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其动机的产生更多地是为了迎合妄想、幻听等病理性内容。而犯罪方式残忍主要存在于犯罪结果危害性大的刑事案件中,精神障碍患者在妄想的支配下杀害亲属甚至是陌生人,造成不良的社会危害性。如南昌红谷滩杀人案,患有躁狂症的男子万某冲向正路过街头的三名女子,从红色袋子里掏出一把刀,毫不迟疑地刺向走在中间的沈某的颈部,致沈某抢救无效死亡。这种祸从天降的恶性伤人事件的发生总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造成社会的莫名恐慌。犯罪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主要表现在犯罪对象、犯罪地点和犯罪方式的选择上,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在地铁上、商场等公共场所实施犯罪行为,通常在实施犯罪行为后,精神障碍患者的逃避意识不强,常被现场抓获。如2018年11月13日一女子称在地铁上被一男子纠缠,后经警察调查,发现该男子系精神分裂症患者,认为该女子是其前女友,称“鞋子在地铁上给了‘前任女友’”。
结合精神病学及犯罪心理学理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意识障碍,犯罪情节严重。重性精神障碍发病期患者常伴有意识障碍,同时,在妄想、幻觉等精神病性症状影响下,产生认知功能障碍或思维错乱。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实施暴力行为比例在所有精神疾病中最高达30%。意识障碍患者实施犯罪的地点、犯罪工具的选择及被害人的选择通常具有随机性,暴力风险较大,社会危害性可大可小。
二是智能缺损,犯罪动机简单。有些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因先天智力缺损,辨别是非能力差,在他人的怂恿和教唆下从事犯罪,甚至被抓后依旧不明后果,不知悔改。如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其智商可能仅限于3岁小孩水平,根本没有法律意识,思维简单,容易被他人诱导实施犯罪,而他们对犯罪的认识仅限于“别人让我做的,说做了之后给我买糖吃”。
三是情感波动,犯罪不计后果。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经治疗缓解后出院居家服药治疗,亲属便是其第一的监护人,若患者服药依从性良好其病情得以控制,情绪平稳,社会适应良好。相反,倘若疾病出现反复,亲属未及时察觉,亲属很可能会成为第一受害人。
四是人格障碍,犯罪持续性强。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通常也称为变态人格(Abnormal Personality),是一种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人格发展内在不协调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人格结构和它的组成部分均衡发展上产生障碍,突出地表现为情感和意志明显偏离正常,而不存在认识过程障碍和智能障碍。人格障碍虽然不属于严重精神障碍的一种,但其社会危害性极大,其中尤以反社会人格犯罪最为常见,这类人格障碍患者对人冷酷无情,缺乏责任心,极端自私,自尊心强,却无羞耻感,故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喜欢做违背伦理道德和社会常理的事情,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再犯的可能性极高。
五是好逸恶劳,再犯风险增加。有学者对某监狱关押的555名重新犯罪人员进行统计后发现,重新犯罪类型中,财产型犯罪比例最高,为38.02%,而这主要与犯罪人家庭条件较差和缺乏社会技能有关。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生活通常需要亲属的照顾,缺乏社会技能,强制医疗虽能够解决其身体疾病,但不太能够培训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技能,绝大多数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在强制医疗结束后依旧无生活来源,懒于做事,生活缺乏归属感,财产型再犯罪风险增加。
二、解析:刑事诉讼中法官与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的良性心理互动
一是悔罪心理。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在疾病缓解期或经治疗后病情好转,其一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产生悔罪心理。此类患者经公安机关教育后,一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并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犯,但是否发生再犯,主要取决于监护人的监管力度和疾病的稳定程度。
二是侥幸抵赖心理。针对那些存在意识障碍或者处于精神疾病缓解期的患者,其针对控诉,通常会予以狡辩,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这类患者狡辩之词通常空洞乏力,不具有查证的必要性。同时,自身疾病通常成为患者侥幸心理产生的源头,认为自己是精神障碍患者,犯罪无须接受刑罚。
三是依赖心理。基于心理年龄的不成熟性,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违法犯罪后通常会产生依赖心理,这种依赖并非犯罪后产生,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因为患者通常没有经济来源,其生活起居均由亲属照料,当犯罪行为发生被抓后,其第一反应便是寻求家庭的庇护。
四是抗衡心理。心理学家认为,人人都试图维护自己的自尊和自由,一旦感到它受到威胁,就会力图去恢复他们,这种试图恢复自尊和自由的动机状态即对抗心理,而这种扭曲的与社会抗衡的心理在人格障碍患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五是积极心理。通常来说,被告在诉讼中解决实体问题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的。然而精神障碍患者在诉讼中可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这种积极的态度往往反常的、不合情理的。如严重抑郁症患者的曲线自杀,其目的就是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以实现其结束生命之目的,因此在诉讼活动中表现为积极主动陈述犯罪事实,承担刑罚。
1.法定代理人的气愤与无奈
在精神障碍患者违法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作为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虽然与被告有同样的诉讼要求和利益一致性,但其中也包含复杂多变的情感要素,既有恨铁不成钢的气愤、自责,也包含对于精神疾病无法根治的无奈,更有对今后如何更好地监护患者的焦虑。在法定代理人面前摆着的一方面是犯罪事实,一方面是民事赔偿,而更让法定代理人感到绝望的是不可预知的“再犯罪”。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被告,根据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由该法条我们可以知道,无刑事责任能力患者在无罪释放后家属或者监护人成为其主要监护主体,在必要时才会由政府进行强制医疗。那么,未行强制医疗患者无罪释放后是否会再犯罪?若再犯罪,其带来的民事赔偿如何解决?这是法定代理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法定代理人心理矛盾之一。
2.辩护人的同情与焦灼辩护人作为被告人一方的辩论专家,其具有专业的法律素养和道德品质,面对精神障碍患者这一特殊的被告人,辩护人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情心理,试图通过精神障碍这一理由,帮助被告人辩护,赢得法官的认同。另一方面,基于精神障碍患者犯罪结果的严重性,辩护人也会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产生担忧,总怕在与被告人交流案情时受到被告人的侵害。最后,由于精神障碍患者病情不稳定,即使被告人在庭审前与被告针对案情达成共识,在庭审时,被告人依旧可能在病情的影响下胡言乱语,这也进一步导致辩护人的无奈、焦灼之心理。
3.原告的恐惧与报复不同类型的原告心理一般有所不同,笔者就原告一般心理予以分析:
恐惧紧张心理。基于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标签效应”和犯罪手段的暴力性的感受,原告常表现出恐惧、害怕、紧张,担心再次受到伤害,甚至可能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突如其来的伤害,也可能导致原告精神过度紧张,不知所措,感知失常,这种情况下原告作出的供述可能与案件事实有出入,但这与作伪证和诬告陷害有所区别,这种错误陈述很大程度是基于紧张心理而产生的生理反应。当然,不同群体其心理素质并不相同,原告在行为发生时和行为发生后心理也可能始终表现正常。其在陈述被害过程时条理清晰,内容清楚,真实可信。在这种情形下,原告针对所受伤害提出的赔偿要求合乎常理,被告方一般也会接受。
报复心理。原告出于对犯罪分子的仇恨、憎恶,夸大案情和自身受伤情况,甚至故意编造本不存在的事实,以期达到严惩犯罪分子之目的。但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是精神障碍患者,这种报复心理可能会基于原告自身的同情心而有所削弱。
同情心理。当原告人身权、财产权受侵犯较轻,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及时道歉并予以赔偿时,原告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同情,产生同情心理。当然,同情心理的产生与原告自身素质、案件性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亦有着密切关联。
4.公诉人的矛盾与优越检察人员在公诉活动中与各种关系人直接较量,必然受到一定心理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法律程序制度以及庭审活动中各类人员心理活动的相互感染和影响。公诉人和法官在惩戒、教育、感化精神障碍被告人上存在心理趋同,但公诉人在诉讼活动中也有其特殊的心理表现:
一是矛盾冲突心理。公诉人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一方面其担负着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另一方面也需要保证控诉事实的准确无误,这种矛盾冲突的心理推动着诉讼活动的开展。
二是优越心理。在精神障碍患者违法犯罪刑事案件中,公诉人具有一定的优越心理,无论是从审判程序上,如公诉人先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先对被告人讯问,还是在实体调查权利的便利性上,如检察机关可以申请对被告人进行司法鉴定,公诉人均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是基于公诉人的法律定位和性质,其优越心理可能会影响案件调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了解诉讼参与人的常见诉讼心理是法官合理应对各方心理变化的第一步,如何预期诉讼参与人的心理变化,制定应对策略,才是司法实践中应当着重考虑之事。
有关域外研究发现,从民众的心理认知角度看,程序的公正与否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对结果的满意度与信任度,相关研究也表明,倘若诉讼参与人感受到程序的公正,即使败诉,其依旧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由此可见,诉讼程序的公正与诉讼结果的可接受性程度存在关联。然而,在诉讼程序较为公正的法治社会,为何还会存在因诉讼结果而产生的上诉、信访等尴尬局面?被告人对诉讼的心理平衡尚未得到相对满足,或许应该得到法官的充分重视。因此,在应对刑事诉讼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时,法官应当在秉承诉讼程序合理合法的基础上,结合诉讼心理学的理论和原则,充分借助学科融合的知识体系,让诉讼纠纷解决更“接地气”,更“合心意”。
一是法官与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的心理互动技巧。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在庭审中一方面可能具有抗拒狡辩心理,面对此情此景,法官不可一味地强调其有罪,应当通过充分的举证,以证明其罪行,同时,结合精神障碍被告人的精神状态,予以简单的心理评估,引导被告人合理合法理性地辩护。另一方面,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庭审时发病。法官应当注意精神障碍被告的言语内容是否合乎逻辑、与现实相违背,如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虽然司法鉴定意见显示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庭审与鉴定相隔时间有长有短,加之庭审环境过于严肃紧张,其精神病性症状可能会出现,如不信任自己的辩护律师,妄想自己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法官勾结,就想判处自己死刑;又如,患者总是在审判席上自言自语,言语常人难以理解或觉荒谬等。面对这类被告人,法官应当及时停止庭审,结合相关人员的意见,明确是否能够继续审判,必要时可进行受审能力鉴定。
二是法官对原告情绪的识别与调和。原告在庭审过程中通常表达出较强的愤怒情绪,强烈要求惩罚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心理和情绪不能受被害人感染,应当保持理性,迅速调整自己的心理情绪,调和庭审氛围,维持庭审秩序,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
三是法官对辩护人的理性识别与善意提醒。辩护人作为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基于其律师的基本素质,其通常能够保持理性,法官应当充分考虑辩护人意见,辨别其辩词的关联性和真实性。针对辩护对象的特殊性,辩护人可能认为精神障碍是最佳辩护理由,因此可能存在信心倍增,无视控诉人之情形,法官在面对此类辩护人时应当及时提醒,有精神障碍不等于无罪,不等于不需要进行民事赔偿,及时逆转辩护人“必胜”的心理,以保证举证的充分合理以及辩护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客观性。
四是法官对法定代理人的释明义务。严重精神障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与辩护人心理有趋同之势,将“精神病”认为是无罪之理由。但法定代理人在庭审中因法医精神病鉴定申请被驳回而感到愤怒和不公正,法官应当充分阐述鉴定申请被驳回的理由,以平息法定代理人的愤怒,让其感受到法庭的公正,这样也有利于提升判决结果的接受度。
五是法官对公诉人的引导与心理转化。面对公诉人在庭审中的优越心理,法官应当有敏锐的观察力,通过公诉人言语轻佻的变化、肢体动作的夸大等细微动作发现公诉人的心理起伏变化,引导、转化公诉人的不良心理反应,让其意识到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代表的是国家公权力的形象,不能因为被告人是精神障碍患者,就觉得自己的辩词稳操胜券。另,若发生重性精神障碍被告公然挑衅或言语辱骂公诉人等情形时,为避免庭审冲突激化,法官可以采用休庭的方式,庭下与公诉人积极沟通,缓和紧张气氛。
综上所述,庭审参与者的心理互动应该是在法官引领下的良性心理交流。对于精神障碍犯罪的刑事诉讼庭审,诉讼参与人各自基于自身的心理诉求碰撞出火花,如何将多方辩论心理之间的杠杆维持以平衡,法官的审判技巧和自身素质便如杠杆之上的砝码,轻则失之偏颇,重则有失法律之威严。
三、融通与架构:刑事诉讼中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心理求衡之路桥架构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违法犯罪后,其身份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常使其陷入惶恐与不安之中,同时,其也承受着来自被害人、公诉人甚至社会的巨大压力。如果法官能够辨析精神障碍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掌握各方当事人心理变化规律,积极引导庭审各方当事人合理充分辩护,这既是对精神障碍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也能够调和诉讼参与人的心里郁结,更能够促进庭审程序的有效推进。
打铁还需自身硬,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要想保持庭审各方良性心理活动,需要具备优良的自身素质,总结归纳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良好的气质素质,如无求无私、无畏无惧、有情有感等;其次,优秀的品质素质,如热爱本职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把控是非界限等;最后,高超的能力素质,如敏锐的观察力,牢固而清晰的记忆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等。回归诉讼实践,法官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诚意之上,读心为计。面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模式下,法官可以适当运用心理学理论,感受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在庭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如心理学中常用的沟通技巧:共情。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所谓共情,就是感同身受他人情感变化的一种行为。虽然精神障碍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这可能是在其无意识的状态下实施的,有些重型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犯罪后可能无法回忆其犯罪的具体过程,如“梦游症”患者,其在睡梦中实施了犯罪行为,醒来后根本不知晓其实施的犯罪行为,针对这样的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应当表现出一定的理解诚意,实现与精神障碍被告人的庭审共情,以诚心沟通“有意识地通过言语交流转移冲突,避免偏激想法的加剧,使当事人能倾诉痛苦感受,排除焦虑、愤怒情绪,从而减轻其心理障碍,回归到案件正常处理上来”。
二是合理满足,把控庭审。庭审中的各方都是奔着其诉讼需求得到满足之目的而坐于庭上,法官对庭审各方合理需求的满足,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在诉讼程序法治化的今天,诉讼参与人的生理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在此不作过多阐述。首先,是安全需要,该需要在庭审中主要体现在“身”和“心”两方面,“身”主要针对的是一般诉讼参与人,主要包括安全的庭审条件、相对稳定的诉讼环境、诉讼参与人的健康状态等;“心”更多的是针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一般的诉讼环境可能并不能实现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安全需要,受精神疾病的影响,可能需要满足一些特殊条件,如特定人的“回避”(如有些精神障碍对穿警服的人有特定的被害妄想,在此类情形下是否可以要求警察便服出庭?)、特定事的“回避”(精神障碍患者通常缺乏自知力,“被精神病标签”效应可能会诱导其不良情绪产生,法官在庭审中是否尽可能“回避”精神疾病等特殊词汇?)。当然,上述回避应当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其次,社交需要在庭审中更多地体现在精神障碍患者陈述权的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亦明确规定,诉讼参与人享有相应的陈述辩论的权利,因此该需要基本能够得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存在思维散漫、思维跳跃等病理性症状,当法官发现其逻辑超乎常理时应当予以制止,以维护诉讼秩序。再次,精神障碍患者自尊需要的满足与安全需要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分强调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疾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精神障碍患者自尊需要的满足。“自尊需要能使社会个体自身达到和谐状态”,合理满足精神障碍患者的自尊需要亦是一种司法“救赎”。最后,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基于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背景,每个人都有其自我实现的需要,精神障碍患者因自我实现需要的扭曲而误入歧途实施犯罪行为,故需要有人帮助其回归正途。自我实现需要强调的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因此,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也应考虑精神障碍患者受审后的自我实现需要,给予相应的鼓励性言语和必要的社区矫正建议,帮助其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三是充分释明,实现共赢。解释技术指运用心理学理论来描述求助者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原因、实质等,或对某些抽象复杂的心理现象、过程等进行解释。一方面法官通过向原告方阐述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阐述刑事和解的法律意义、社会意义,解除其心理障碍,以谅解精神障碍被告人,实现刑事和解效力最大化。另一方面,法官向被告方阐述有病不等于无责之法律意义,分析庭审中争议点评判的主要法律依据和科学依据,增加被告方对判决结果的内心确信。解释技术的运用效果更多取决于解释者自身的综合素质,因而,法官在实践中可以不断总结类案经验,提升自己的沟通解释技巧,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
著名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贝格说道:“法官在法庭上不向心理学家咨询,不向心理学家请求对暗示的现代研究可以提供的所有帮助,就从事司法工作,这似乎是令人感到惊讶的。”而将心理学相关专业人员和心理学技术运用于庭审中在域外亦并非无从循迹。
首先,精神卫生法庭模式对法官架构与精神障碍患者沟通的桥梁有借鉴意义。精神卫生法庭(Mental Health Court)是一种特殊的法庭模式,专门用于处理患有精神障碍的被告/罪犯的刑事案件,属于“问题解决型(problem-solving)”法庭模式的一种。精神卫生法庭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以设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联合沟通的本质。精神卫生法庭通过法官、检察官、律师、精神卫生专家、案件管理人、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缓刑官或者保释官以及患者家属的合作,将卷入司法系统但是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者送往合适的机构接受治疗。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协调处理各方角色任务,是精神卫生法庭设立的核心作用。我国目前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精神卫生法庭,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借鉴其核心理念——融合各方力量,针对性开展精神障碍刑事审判活动。因此,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应积极听取诉讼各方意见,准确把握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状态,必要时可以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合议,甚至可以根据严重精神障碍的种类构建精神障碍患者精神卫生庭审案例库,为今后精神障碍患者审判工作开展积累经验。
其次,专人介入,为审前心理评估护驾。一次庭审的顺利进行并非一方之力,法官在面对精神障碍患者时,专业知识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审判。为充分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状态,破解法官的知识壁垒,有必要在诉讼前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心理评估。鉴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特殊性,评估小组成员组成应当包含精神科医生或者具备资质的法医精神病鉴定人。根据评估结果,法官可以充分了解被告人的精神状态,便于知己知彼全面了解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和环境要素。该心理评估可以在侦查阶段完成,也可以在审查起诉前完成,既便于公诉机关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也为是否需要后续是否需要进行强制医疗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另,为保障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心理评估的时效性,笔者认为庭审前实施简化心理评估很有必要。
最后,法官当审慎“锚定效应”,注重庭审实效。所谓“锚定效应”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下,判断与决策的结果或目标值向初始信息或初始值即“锚”的方向接近而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有相关证据(如精神病家族史、精神病史、行为异常、证人证言等)表明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病时,公安机关会启动鉴定程序,得出鉴定意见,并随案件移送。法官在审前查阅案件材料时,鉴定意见书是其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精神病的重要材料。鉴定时具有精神疾病是否意味着庭审时无法积极参与庭审?又或者说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就能如常人一般配合法官,推进诉讼程序?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司法鉴定意见仅是证据链中的一个环节,更何况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信度不足常为诟病。面对“多次鉴定的不一致性较高,由此引发较严重的重复鉴定、多次鉴定”法官该如何抉择亦是难题。为此,法官应当审慎对待因鉴定意见带来的被告患有精神病或无精神病的“锚定效应”,在庭审前充分审查案卷材料,结合多方调查,形成自己内心的初步确信。以这份自我确信为矛盾,在庭审过程中寻找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的蛛丝马迹,进而形成合力,高效推进诉讼进程。
“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性的动物”,更何况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诉讼纠纷的解决“既要有文对文,也要有面对面的辅导”。诉讼辅导是指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辅导人员与诉至法院的人民群众通过沟通交流,了解其诉讼心理和真实诉求,开展诉讼常识和诉讼风险的辅导,引导建立正确的司法认知,帮助人民群众寻求适当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系列活动。诉讼辅导目前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的诉前诉中和诉后环节,旨在帮助人民群众了解诉讼程序,提示诉讼风险,引导其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
在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参与刑事诉后环节嵌入诉讼辅导有其必要性。一方面,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对判决结果的理解程度较低,部分被告人不信任代理律师,第三方中立人员的解释更容易让被告方信服,进而可有效节约诉讼资源,避免“案结事不了”。另一方面,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诉后心理矫正和监护需要专业人员给予专业意见,有关规定表明,诉讼辅助人员可以由法官及心理咨询师等人员担任,心理咨询师的介入能够提升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也能够为监护人或者监狱监管人员提供必要的监管意见。
在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参与的刑事诉讼案件中引入诉讼辅导制度的核心是利用专业人员的技术优势,弥补法官之不足,提升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诉讼辅导人员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审理法官在诉讼辅导人中的定位有待考量。在面对案件增多和一些当事人的非理智的激烈情绪的双重压力下,特别是在已经经历司法程序形成结论当事人又兴师问罪的情况下,要求案件审理法官要完全做到耐心解释、实现释明效果是有困难的。另外,法官虽然具有超于常人的法律知识体系,但部分法官沟通交流之技术并非超于常人。为此,引入心理咨询师、精神病医师或法医精神病鉴定人(以下简称第三方机构人员)参与诉讼辅导或许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较于审理法官,第三方机构人员承担诉后答疑咨询更能有效保证“案结事了”。另外,心理咨询作为精神障碍的治疗手段之一,心理咨询师亦更了解精神障碍的病理机制,法律专业人员积极耐心解答严重精神障碍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法律困惑,第三方机构人员积极关注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变化,二者相辅相成,能够有效节约审判资源,提升诉讼效率。最后,诉讼程序是高度程序化的纠纷解决模式,“诉后答疑+诉讼辅导”更多地是在法律的“威”和“信”之间的平衡杠杆,因此,法官的主导作用依旧不可忽视。构建以非审理法官为中心,第三方机构人员为外围辅助人员的诉讼辅导小组,既符合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也有利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诉后心理调适,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方机构人员的诉后介入一方面有利于“案结事了”,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精神障碍患者家属后期履行监护职责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有研究显示,湖南省2005-2009年1808例违法的精神病人,接受强制治疗者只有284人(15.7%),未接受强制治疗者有1524人(84.3%),而在实施治疗的案例中,由家属执行的有117例(81.8%),侦查机关直接执行的只有24例(16.8%),法院裁决侦查机关执行的只有2例(1.4%),由此可见,亲属在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医疗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实践中亲属是否尽职监护确有待考量。有些亲属因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行为产生恐惧,因而拒绝接回家看管;另外有些患者其精神疾病隐蔽,平时言行与常人没有太大区别,亲属便疏于管理,造成精神障碍患者再犯罪的局面发生。而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重要因素是亲属对于精神障碍疾病的不了解,因此,合理正确落实亲属的看护职责,需要有专业人员给予辅导和帮助。必要的精神病护理知识宣传,再犯罪的有效预防,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解除后的生存技能培训等均是亲属履行监护职能的必备要素。然而,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和事后预防并不仅是亲属和法官的职责,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构建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整体联动机制、落实分类管理措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一系列措施需要政府、社区、亲属等多方力量协同出力,结合我国司法立法实践不难发现,我国在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综上所述,诉讼辅导在解决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参与的刑事诉讼案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诉讼心理学对于诉讼规律的探索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冲突纠纷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其扎根社会的病理根源,随着文明社会的产生,人们选择由第三方如国家来处理纠纷。而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则繁荣发展,法官在诉讼冲突解决中的位置愈发重要,如何更好地将精神病学、心理学知识和技术融合于司法审判也是今后司法审判进一步需要考量的问题。
结语
心理学及精神病学在司法审判中的介入对于调和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的诉讼心理落差,缓和诉讼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法院审判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法官如不掌握相应的心理学知识,将很难应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参与的刑诉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无论是诉前心理评估,还是庭审中审判技巧的运用,乃至诉讼辅助制度的诉后调适,都具有鲜明的诉讼效用,因此,新时代法官应当重视诉讼心理学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往期精彩回顾
课题组|上海市行政执法现状与规范化路径研究
杨骁瑜|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居委会功能与定位的重塑
吴向芸︱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的立法模式及制度构想
于启航︱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机制研究
刘连康|司法大数据应用事务外包的风险与防范研究
张曦|诉讼构造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民事诉讼事案解明机制构建探索